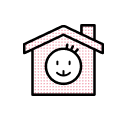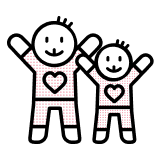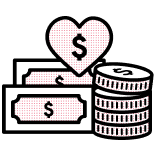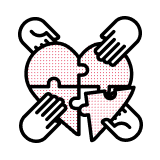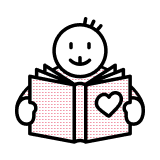基金會與顱顏家庭闖過每一個關卡,直到顱顏孩子成為懂得感恩的大人。因為這份不離不棄的陪伴服務,讓基金會在「社會投資報酬率」 拿下 17.4 的分數。
代表捐款的每 1 塊錢, 基金會以 17.4 倍的價值投入到社會。
代表捐款的每 1 塊錢, 基金會以 17.4 倍的價值投入到社會。
社會投資報酬率 (SROI) 意指衡量在投入資源後,所得到「非財務面」的回饋與報酬,例如社會影響力、環境永續性等。
一般而言,在計算一組織的社會投資報酬率時,會衡量其所達到的經濟價值、社會價值、與環境價值。投資者也可採用其他指標來評估,例如文化價值、社區價值等。
一般而言,在計算一組織的社會投資報酬率時,會衡量其所達到的經濟價值、社會價值、與環境價值。投資者也可採用其他指標來評估,例如文化價值、社區價值等。